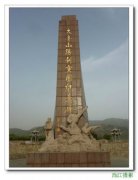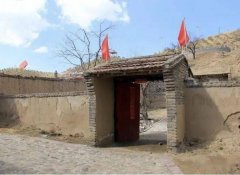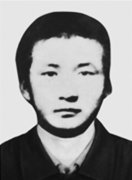红色故事:革命春秋昭后世
革命春秋昭后世
——记“辽吉功臣"吕明仁烈士
刘忱
1947年4月12日,中共辽吉一地委书记、军分区政委吕明仁,在奈曼、开鲁交界的西辽河为抢救落水的警卫员不幸遇难。噩耗传出,辽吉人民痛伤万分,中共西满分局、辽吉省委、哲盟工委、开鲁县委等各级党委为吕明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吕明仁的灵柩由开鲁运抵齐齐哈尔市时,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、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等领导同志,亲自到火车站迎灵。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、省政府主席阎宝航等领导同志轮流守灵。省委组织部长曾志和地委秘书宋树功为吕明仁写了传略。追悼会上,陶铸同志亲致悼词,高度评价了吕明仁短暂而光辉的一生。1947年9月30日,中共辽吉省委决定:追授吕明仁同志为“辽吉功臣吕明仁,原名吕其惠,1916年12月9日出生于奉天省庄河厅(今宁省庄河县)大王家岛一个贫寒的渔民家庭。六七岁时,他就帮助家里放猪、割草,有时还和父亲、哥哥一起下海捕鱼捞蟹。艰辛的童年生活,培养了吕明仁勤劳、勇敢、机敏的性格。目不识丁的父亲发誓:宁肯自己累断腰脊,也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。1922年,吕明仁进了小学,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,学习上非常用功。1926年,吕明仁考入了石城岛高级小学。每天和小朋友们一起划船到十几里外去读书,风吹浪打,从不缺课。文化知识的启迪,惊涛骇浪的洗练,促使了吕明仁的早熟。他常常提出一些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问题:为什么越拼死拼活赶海的人越穷?为什么那些不下海的人能吃到山珍海味?警察就可以随便打人吗?!这时的吕明仁看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和人世间的不平。带着这些问题,他决心发奋读书,探个究竟。1929年夏,吕明仁考入了庄河县初级中学。1931年,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“九一八”事变,很快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。家乡沦陷,山河破碎,激起了吕明仁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。1932年,他愤然离开家乡,与胞兄吕其恩、堂兄吕其恕,流亡到山东烟台第八中学(后称山东省立中学)求学。国民党"攘外必先安内"的卖国政策更使他痛心疾首。国难当头,他和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一样,积极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烟台学生抗日救亡斗争,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。他参加游行、演讲、散发传单等活动。为此学校开除了吕明仁。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职业革命征途,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,这时,他年仅16岁。
1934年,吕明仁赴北平弘达中学高中部学习。这是党组织安排他以读书为掩护,在地下党员柳文广的指导下做秘密交通工作。弘达中学当时是一占与众不同的学校,办学者是5位东北人,学生基本上是从东北流土来的青年,校方很重视抗日救国思想的教育,师生中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。在弘达中学读书期间,吕明仁经常往来于北平、天津、烟台等地,为党组织传递秘密信件,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,赢得了党的信赖。1935年8月,经温建平同志介,绍,吕明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1935年秋,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动华北“自治”。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",吕明仁参与组织了“一二•九”学运工作。 '
后来他从一张秘密传单上得知延安红军大学招生的消息后,便与爱人丁修等同学商定,决定前去报考。恰巧,这时山西军阀阎锡山在北平招募一些青年,充实其部队。于是,党组织决定让吕明仁等100余名学生跟随薄一波同志到山西去,待机转赴延安。
到延安后,吕明仁入抗日军政大学(原红军大学)第十三大队学习。半年后结业。吕明仁留校担任一大队政治教员。为了完成党交给的讲课任务,他博览马列著作,呕心沥血认真备课。他讲课深入浅出,循循善诱,很受学员尊崇,不久,被提升为政治主任教员。期间,由于用脑过度,吕関仁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,经常头痛,甚至难以入眠。吕明仁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,从未影响过工作,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。七七事变后,吕明仁就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请,要求到抗日前线去。1939年夏,党组织批准他的请求,让其随“抗日军政大学总校”东征到太行山区。1940年初,到达太行山区"不久,又转战到山东胶东区,担任胶东区委宣传部部长,兼任区党校校长和区党委农村工作团团长。
他努力团结各阶层人士,开展减租减息工作。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,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,巩固了抗日根据地。
1942年,日寇发动“大扫荡”,胶东区西海地委遭到严重破坏,地委书记余己午等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光荣牺牲,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。在险恶形势下,党组织派吕明仁任西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,他毫不畏缩地挑起重担。学习用兵打仗在险恶中求生存,求发展。经过艰苦的斗争,又重建了西海根据地。
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,党组织又派吕明仁同志到东北开辟新区工作。当时,他的爱人丁修去山东分局开会未归,吕明仁毫不犹豫地将出生不满百天的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,立即启程。在去东北的船上,吕明仁遇到离别十几年的叔叔和胞弟。家中原以为他牺牲了,偶然相逢,叔侄百感交集。叔叔和弟弟劝他顺路到家看望日夜盼念他的父亲和母亲,婉言回绝了叔叔和胞弟的劝说,急公兼程,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优良品德。此后,他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。
1945年9月末,吕明仁来到辽西煤都——阜新,任阜新工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。当时的阜新,情况极为复杂,日伪残余为非作歹,破坏矿区生产,盗窃资财;土匪蜂起,四处抢掠,残害百姓;国民党网罗地痞、流氓,拼凑反动武装。面对这种形势,吕明仁亲自深入矿区,访贫问苦,发动矿工锄奸反霸,组建工会,开工生产。同时,他又扩建了以矿工为主体的武装部队——66团、68团,亲率这支队伍,击溃了国民党“中央自治挺进军”解放了彰武。随后,他又乘胜出兵,追剿阜新、彰武、黑山、北镇一带的地匪和地主武装,。
由于操劳过度,他的身体日渐衰弱,组织决定为他增加营养,被他婉言谢绝。当时,地委的伙食不如区委的伙食好,吕明仁同志则嘱咐身边的同志们说:“我们住在城里,总比在乡下工作的同志环境好得多,应该多照顾他们的生活。"日伪投降时,在阜新丢弃了大量物资,从军需物资到日常生活用品无所不有,其中有许多是稀罕之物。这是战利品,作为主持地委和军分区工作的吕明仁,既有随时调用分配之权,又有堂而皇之调用之理,况且当时新建的地委机关和分区机关确实一无所有。然而,吕明仁没有这样做,他从革命的大局出发,首先把更多的物资上缴给主力部队,解决军需困难。按照先救济群众、后基层、最后地委机关的顺序分发下去。
1945年11月中旬,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后,东北的形势迅速紧张起来,我党釆取了退出城市到农村去,“让开大路,占领两厢。"的策略在12月2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》的指示中,明确指出:“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,是建立根据地,是在东满、北满、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。”吕明仁率领地委全体同志于12月30日撤出阜新,转移到阜新北部农村福兴地一带。在转移时,他号召地委机关每人背出一匹布,自己同大家一样,也背也了一匹布和两支枪,并且与警卫排一起,断后打匪,掩护转移。
1946年2月下旬,根据中共辽西省委指示,吕明仁率领阜新地委转移到通辽,在新四军三师手中接管了通辽、开鲁两县。为适应新的情况,阜新地委改为通辽中心县委,吕明仁任书记。当时,有的同志因降级使用而闹情绪,甚至产生思想波动,吕明仁相腹从公,及时教育大家要端正认识,振奋精神,克服地位观念和名利思想。
通辽、开鲁是哲里木盟中部的两个汉人聚居县,四周与蒙古族群众聚居的旗毗邻。这里革命基础薄弱,14年的日本法西斯统治及其民族挑拨政策,使蒙汉民族之间形成了一条沟壑。日寇投降不久,国民党反动派就在通辽公开组织党部,拉匪建军。1945年10月下旬,中共辽源(今郑家屯)工委就在这里建立了通辽工委和民主政府,并委派共产党员杨德明任通辽工委书记,徐永清任通辽县县长。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动下,于12月8日通辽县保安总队发生叛乱,逮捕并杀害了我方29名干部,制造了震惊东北的惨案。通辽中心县委在吕明仁同志的领导下,打击了国民党分子的反动活动,清除了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;迅速开展了反奸清算的群众运动。同时,组建了县、区、村各级人民民主政权,建立了县区武装,消灭了为患多年的“大金龙”箸股匪。
吕明仁非常重视民族问题。他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,努力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,积极帮助蒙古族的民族自治解放运动。在阜北农村时,他派出地委干部到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带进行蒙区社会情况调査。他根据民族工作的需要,在县政府设立了“蒙民自治科”,继续开办了蒙古青年学校,在当时干部奇缺的情况下,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本地民族干部,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。
1946年4月下旬,中共西满分局、辽西省委决定,在通辽中心县委的基础上建立辽西五地委,吕明仁同志任地委书记,辖通辽、开鲁两县及科左前旗、科左中旗、科左后旗、库伦旗、奈曼旗等五个蒙古族聚居旗。同年5月中旬,通鲁警备区与东蒙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二师组成蒙汉联合司令部,吕明仁兼任政委。同年6月初,在通辽建立哲里木盟政府,吕明仁又兼任盟政府副主席。从此,哲里木盟,实现了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。
1946年10月,国民党军队大肆向哲里木盟进攻。10月;下旬,国民党出动其“王牌'‘七十一军一个师的兵力,东从郑家屯,南从彰武两面夹攻通辽,来势汹汹。吕明仁临危不乱,他按照省委的指示,沉着冷静地组织军民转移。敌人攻进通辽城东门,他才带领地委机关干部最后从西门撤出。撤出通辽后,他将通辽、开鲁两县的干部编成武工队,称“长江骑兵团”,他亲任团长兼政委,坚持在哲盟北部开展游击战争。取得了哈拉吐达战斗的胜利,振奋了军心。从通辽撤出时,吕明仁的左背生了疽疮(俗称“瘩背疮”),因紧张的战斗生活,未能得到及时医治,日见恶化。1946年12月下旬,省委通知他去白城子开会,当时,他高烧达41度,同志们劝他请假休息,可是他不顾个人的安危,拖着病体,冒着严寒,由高力板乘马按时赶到省委,未及开会就昏迷过去。当即被送往医院抢救,经两次手术才脱离危险。躺在病床上,他还惦记着工作,当同志们去看望他时,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病了好久,许多事堆起来没有办。”
伤口尚未完全愈合,他就急着出院。当领导和同志们来劝阻时,他却安慰大家说:“我知道,不要紧,几天就全好了。”也正是在他住院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辽吉省的大部分地区。根据形势的变化,辽吉省委于1947年1月决定:一、五地委合并,统称一地委,吕明仁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。2月初,吕明仁率领原一、五地委撤出的干部再插回原地,恢复这两个地区的工作。省委书记陶铸、省委组织部长曾志亲自从白城子赶到沸南,为他们南下送行,预祝胜利。
在收复一、五分区的战斗生活里,吕明仁忍着疮痛,跃马横枪,率先垂范,解放奈曼、收复科左后旗,直指库伦、康平。经过几次大的战斗,一、五分区局面有了很大恢复。康平敖力营子一战,击溃了国民党“东北长官部”装备最精良的特务团一个营,大大鼓舞了军民士气,震慑了敌人。每收复一地,吕明仁总是立即传达上级指示,接着就布置工作,继续向敌后挺进。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,甚至要请示上级,他总是那句话,“我知道,不要紧,没系”。党的利益、革命工作高于一切,心中唯独没有他自己。
4月9日赶到开鲁,立即召开会议。4月11日深夜,他正在主持会议,突然接到省委的紧急军务电报。当夜,会散得很晚,他席不暇暖,次日凌晨便匆匆离开开鲁,准备返回一地委所在地一奈曼旗大沁他拉。开鲁与奈曼之间隔着西辽河,百余米宽的河面,水流湍急,浊浪翻滚。辽吉4月,冰雪初融,春寒料峭。吕明仁带领警卫员康殿才和通讯员周潢澄策马来到辽河渡口,恰值船夫不在,无人摆渡。茫茫辽河,滚滚东流。任务紧急,时不我待。吕明仁伫马河岸,心急如焚。他毅然决定趟冰涉水过河!
在顺利渡过两股激流、进入第三股激流时,突然一块冰排将康殿才撞落水中,没入激流。在这生死头头,吕明仁毫不犹豫地扑人激流,抢救康殿才。然而水深流急,出生岛上渔家、素习水性的吕明仁,因背疮手术尚未痊愈,加之连日劳累,体力亏虚,几次拼游都没能接近康殿才。反倒被混浊的河水吞没了,通信员周潢澄这时已陷入淤泥,不能自拔,他瞪着模糊的泪眼,望着吕明仁、康殿才在激流中沉浮,便急中生智,鸣枪报警。附近的人们闻声赶来,“吕政委!"“明仁同志'‘的呼声回荡在辽河之畔,震颤了科尔沁草原。船夫跑来了,连衣服也没脱就扑入河中。吕明仁同志从激流中被拖出,但因肺中呛水,抢救无效,辽吉人民的好儿子、我们党的好干部吕明仁,不幸与世长辞了。正是31岁的盛年!
吕明仁牺牲后,中共辽吉省委机关报——《胜利报》,于1947年5月7日以3、4两版发出“追悼吕明仁特刊”,中共开鲁县委作出《向吕明仁同志学习的决定》,通辽、开鲁、奈曼、白城子等地为了永昭功烈,教育后人,以“明仁"的名字命名了街道、学校、医院、乡、工厂。
吕明仁的灵柩安放在齐齐哈尔市革命烈士陵园,中共辽吉省委为他立了碑,刻英名于石上,记丰功于永恒。